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牧童的歌声在荡漾……”翻开记忆的相册,思绪徜徉在儿时的童谣里,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来自乡野的泥土气息。
我生在农村,长在农村。小时候,一到春天,爷爷奶奶就要开始春耕的工作了:犁地、播种、插秧……小时候,家里养了一头老黄牛,那是爷爷用来帮忙干农活的。听说,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,爷爷和父亲去北流的姑姑家牵回来的。那个年代没有车运送黄牛,他们足足走了三天三夜才回到家。从那之后,那头黄牛就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了。黄牛很忠实,自从有了它之后,我们家的一亩三分地年年都有好收成。
那时候的春耕时节,东方的天空上刚刚亮出鱼肚白,村子里的妇女们已经起床,生火烧水。男人们早已开始赶着牲口忙碌了。爷爷奶奶也不例外,等我起床时,早已看不到他们的身影。等我赶到田里时,放眼望去,有赶牛犁田人,有弯腰插秧、拔秧人,也有头戴斗笠提桶撒肥的人。儿时的插秧苦中带乐,累中含趣。
上初中以前,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,我和弟弟走在身后,爷爷牵着牛,奶奶挑着竹簸箕。插秧前,我跟奶奶先到秧田拔秧。爷爷则到田间把犁耙扎好,在犁耙前挂上套牛的工具,再把牛拴上。爷爷和老黄牛在田间来回穿梭,把田里的水和泥耙成浓稠的泥浆。随后,奶奶便把秧苗运到田里,我们就可以抛秧了。
爷爷奶奶挽起裤脚踏入水田,我和弟弟依样画葫芦,小脚丫子刚碰着水,就发出“嘶”的一声,连忙把脚收回田埂上,田里的水实在太冷了,过了好一会儿,我们才适应田里的水温。我照着奶奶抛秧的样子,把秧苗抛到田里,但是没有像奶奶那样抛得整齐。
过了晌午,我们便在田间地头休息,喝着奶奶早上从家里带来的粥,配上萝卜干。那时候总觉得,拿去田里的粥才好喝,没有菜也能喝上一大碗。吃过午餐之后,我们又继续回到田里工作,虽然很累,但是觉得很充实。
我们村子里的农田都是连在一起的,但是界限分明。山坡上到处都是春耕的人家,高高低低的坡地上,时不时传来吆喝声、牛叫声、响鞭声。家里的大黄狗便在田间地头跑来跑去撒欢,弄得浑身脏兮兮的。放眼望去,春光明媚,微风和煦,一幅幅美妙的农家春耕图,就这样遍布山川,流泻田野。
在爷爷去世后,家里便不再种稻谷了,水田让给亲戚种不让其荒废,而旱地奶奶则用来种菜。在农民心中,土地是他们的根,他们同时依恋的还有苍茫大地之上,散发着的浓浓泥土气息。村子里的人不会让土地荒废,这是因为他们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往事随风,一晃而过。现如今,机械化生产代替了牲畜和人力手工劳作,以往的牛拉小犁耙早已不见了踪影,各种各样的拖拉机在田地间劳作。庄稼人终于从传统的农耕中解脱出来,但他们收入不减反而增加了,皆大欢喜。
记忆中的春耕画面已经成为历史,但每到春耕时节,村子里的农民还是会扛着锄头,到田地间劳作,不忘养育着我们的土地。
覃坤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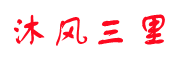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