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暖花开,万物生发,各种鲜嫩的芽菜纷纷上市。我家春天的滋味,是从一盆豆芽开始的。黄豆芽、绿豆芽、黑豆芽、红豆芽……五颜六色、由种而生、生生不息,应时应景、寓意良多。
俗语说:“春吃芽,夏吃瓜,秋吃果,冬吃根。”古人认为芽菜最适合春季吃,一年之计在于春,从现在开始要为健康做储蓄。醋溜豆芽、豆芽拌粉皮、豆芽炒面……奶奶做的豆芽菜是我童年里关于春天餐桌上的大部分记忆。
小时候,每到春天,奶奶都会发豆芽。粒粒饱满坚硬的豆子,摇身一变,化作了嫩嫩的豆芽,这个过程特别神奇,我经常观摩奶奶发豆芽。发豆芽可是一个技术活,选豆洗豆、烫种催芽、换水养芽,那都是有要求的。奶奶将大小匀称、颗粒饱满的绿豆,洗净后倒进瓷盆里。接着烧一锅水,等水晾凉至似烫又不烫手指了,赶紧倒入装好豆子的瓷盆里再焖上盖子,放在暖和的地方。只见豆子慢慢吸收水分,绿色因为水的滋润,更透出灵性。
第二天一早,我急忙跑去看豆子,惊喜地发现豆子慢慢冒白头了。奶奶说,等到白头普遍了,就要开始换水。此后的每天清晨,我都看奶奶给豆子换完水,才开始洗漱、吃饭、上学。一粒粒豆子每天都在变样,竞相生长,就像一群淘气的小精灵,活泼而有灵气。
静置三天后,豆皮儿束不住里面涌动的生机,被撑开一条缝隙,露出里面的豆瓣儿。大约十天左右,当我看见豆芽皮儿剥落、毛根根快要分岔时,豆芽就差不多养好了。这些为春天而生的豆芽,也叫“发”豆芽,取“发”字,自然是为了讨个好彩头。慢工出细活,在不紧不慢的节奏中,时光悠悠长长地走,豆子的清香丝丝缕缕地弥漫。
明代陈嶷《豆芽赋》曰:“金芽寸长,珠蕤双粒,匪青匪绿,不丹不赤,宛讶白龙之须,仿佛春蚕之蛰。”豆芽美好的意境,让人不免想到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高洁。
了解过豆芽的“前世今生”,对它的感情更深了一层。奶奶也一样,豆芽到了她手里,她会最大限度地把豆芽的美味全方位展现出来。奶奶给我做的清炒绿豆芽,可谓是色香味俱全,看着颜色鲜明,吃着脆爽可口,一股春天的味道填满了我的童年,吃着它似乎就会感受到春天的阳光。
时光悠悠,我在春豆芽的陪伴中渐渐长大了,那种味道,留在了舌尖,也留在了心底。如今食物如此丰富,开春后大鱼大肉吃腻的时候,我总会买来豆子,也会像奶奶一样,生一盆豆芽,几天后每根豆芽儿都生了根,像一只只小手,生机勃勃,抓拽着彼此。一根根红豆芽紧紧地靠在一起,安静地生长在盒子里,远远望去,就像一片桃花林。就这么一次小小的发豆芽,心情就此有了一份欣喜。
我用原汁原味的豆芽菜来调剂味蕾,更是为了吃出那份情怀。正像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中所说:“中国人对食物的感情多半是思乡,是怀旧,是留恋童年的味道。所以,我们善于用食物来缩短他乡与故乡的距离。”
清欢有味春豆芽,年年岁岁总关情。
彭宝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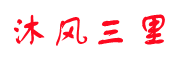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