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拜年,拜年,苞谷花儿上前。” 这是我小时候的童谣。苞谷花儿就是铁锅炒熟的玉米粒。那时流行“拜跑年”,就是从生产队东头跑到西头,或者从北边跑到南边,挨家挨户拜年。我和一群小伙伴儿相约“拜跑年”。每到一户,大家异口同声:“随意叔,新年大发!”“李婶,恭喜发财!”“胡二奶奶,拜年啦!” ……
每户人家都笑脸相迎,端出一盘苞谷花儿,家境好些的还有葵花籽。我们一人抓一把,装进上衣或裤子荷包,欢呼雀跃奔向下一家。
胡二奶奶喜欢小孩子,我们上门拜年,她紧挨我们坐下,沟壑纵横的脸上满是慈祥。她一一询问我们多大年龄、上几年级。我们吃着苞谷花儿,胡二婶(胡二奶奶儿媳)又给我们每人盛一碗甜糟。我们吃完甜糟,很有礼貌地道别。
那时候,我和妹妹,还有几个表兄弟姐妹,都喜欢去金菊小姨家拜年。每次上门,金菊小姨都会拿出好多花生、瓜子,还有糖果、饼干等点心,叫我们大饱口福。有时,金菊小姨和杜家姨父还要留我们吃饭。饭桌上,不但有鸡和鱼,还有稀罕的牛羊肉。这让我们大快朵颐,也大开眼界——我们个个吃得肚子圆鼓鼓的。
金菊小姨是村小民办教师,杜家姨父当兵转业分配到镇上税务所工作,吃商品粮有编制。在生产队,他们属于富裕人家。
在金菊小姨家,我们获得感与幸福感爆棚。多年以后,这种富足受用的感觉仍是记忆犹新。每每想起,仿佛一颗石子抛掷湖面,荡漾一圈圈美丽的涟漪。
“拜跑年”是乡村孩子们的“游戏”,大人很少这样。大人会带着孩子去亲戚家拜年。“千里送鹅毛,礼轻仁义重”。亲戚之间拜年,须携带礼物,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是长辈的,登门更不宜空手。
每年正月初一,我们都得起大早,母亲带上我和妹妹去外婆家拜年。刚走到外婆家门前,我就扯起嗓子喊:“婆婆(襄阳方言,指外婆)、舅舅、舅母,拜年啦!”外婆、舅舅和舅母喜笑颜开迎上来:“恭喜红娃子又长一岁!”然后,大人们进厨房忙碌,我和老表们在外面放鞭炮玩耍。
当年,一包白糖和一瓶白酒为乡村拜年礼品标配。一包白糖一斤,八毛钱。一瓶白酒是本地产五十三度纯粮食酒,酒瓶形状很像弹花锤,俗称“弹花锤酒”,三元五角一瓶。1987年我刚参教,见习期月薪46元,次年转正60多元。
有一年正月初四,我随小爹还有两个堂兄弟一起,去莲英小姑家拜年。我们骑自行车,半小时左右就到了。莲英小姑出嫁快十年,当她看见娘家人出现,十分高兴。赵家姑父也是热情万分,连忙招呼我们进屋,请我们到火塘边坐下。疙瘩火熊熊燃烧,空旷的房间温暖如春。
我们悠闲地喝茶、吃花生、嗑瓜子,赵家姑父说:“你们莫着急,我去厨房帮忙填柴(鄂西北方言,往灶膛送进柴火)。饭很快就好!”
不到半小时,厨房就飘出诱人的肉香。开饭了,满桌子盛席,热气腾腾,香气四溢。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碗排骨汤,排骨占据大半碗。
那时候,农村普遍贫穷,一副猪肝可以待客一个正月——猪肝是很好的下酒菜。腊月间,家庭主妇们将猪肝腌在罐子里。拜年期间,若有客人上门,家庭主妇即取出一二两猪肝,加入白萝卜或胡萝卜爆炒。一盘萝卜炒猪肝,只见萝卜不见猪肝,却有浓浓的猪肝香味。不少人家待客,瘦肉炒萝卜,瘦肉亦是星星点点,难以觅芳踪。
莲英小姑不是这样。她用半副猪肝炒萝卜,猪肝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主导地位,萝卜反而稀少。瘦肉切得像饼干那样醒目。
一碗排骨汤下肚,周身暖和巴适。赵家姑父又为每人斟满一杯“弹花锤酒”。那年,我十七岁,正上师范,也喝了大概二两酒。平日,乡亲们大多喝散装白酒,一斤七八毛钱。“弹花锤酒”属原装,在农村算是好酒。
酒足饭饱,我们要回去。莲英小姑和赵家姑父怎么也不答应,坚决要我们吃过晚饭再走。莲英小姑更是风风火火跑到稻场边,将我们停放在那里的自行车全部锁上,拔下钥匙藏起来。我们遂半推半就留下。晚上,又是好酒好菜招待。我们都喝得晕晕乎乎,吃罢饭,又坐到火塘边烤火,天南海北“侃大山”,简直流连忘返。
莲英小姑家与我们并非山水相隔,我们去拜年竟然留宿一晚。乡村民风淳朴待客实在,由此可见一斑。
抚今思昔,拜年犹如看不见的经纬线,把乡风民俗与人情世故穿连;又像一块巨大的显像板,将社会演进与时代变革清晰呈现。拜年习俗蕴含浓郁的人间烟火气,如果你读懂了拜年,你就读懂了中国乡村乃至华夏民族的前世今生。
涂启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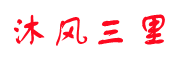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